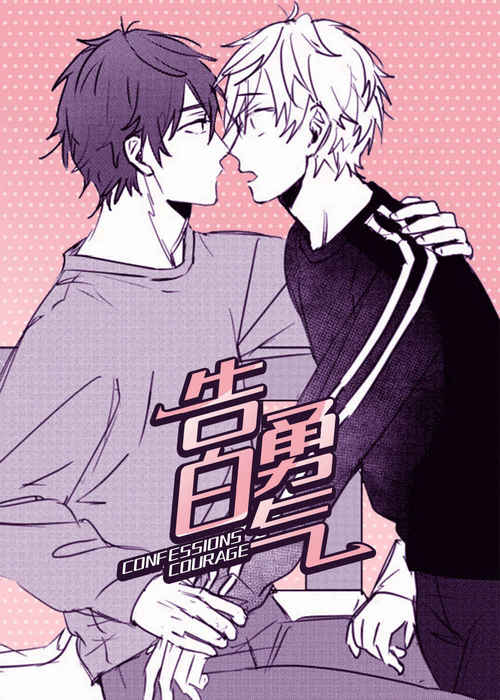美剧,权力的游戏「世界杯 女足」
近期最火的综艺节目,莫过于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三季。拥有前两季的观众基础加上热度的累积,一开播就引发了高度热议。这档综艺节目集结了来自娱乐演艺界的多位30 优秀女性,从第一场初舞台solo到第一次的团体表演,每位姐姐都展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美。
有如王心凌的甜美,朱洁静的柔美,也有如宁静的张扬之美,于文文的帅气之美。当她们为舞台全情投入,绽放属于各自的美丽时,不由得让人感叹,所谓“女为悦己者容”的传统观念,早已过时。
事实上,“女为悦己者容”作为过去广泛的共识,发展到当下俨然已成“女为己容”。女性通过不断成长,也逐渐明白美貌并不能给予自身真正的权力,涂上大红唇画上飞扬的眼线也不会逆转人生。女性不再把自己置于宏大叙事中去成为某种代表,而是在缩小的日常生活里,像弥补人生中的缺憾一样通过“妆容”给予自己一个新的身份。
插画 by Penny
美是谁的权力?
古希腊德尔斐神谕(the Delphi Oracle)里有一个著名的句子:“最美的,也是最正义的。”千百年来“美”就是女性的正义,追逐美丽亦是女性的使命。似乎唯有芳龄永继,才能让女性体面地生存下去。
“德尔斐神谕”源自3000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阿波罗神殿
没有人能否认,拥有美貌就拥有了某种权力。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常年挂着女明星艳惊四座的妆容,欧阳娜娜的“财阀千金妆”,鞠婧祎的“氛围感妆容”,都成为女孩们争相仿妆的模板。我们时常听说,谁又因为貌美嫁得良人,谁又因为整形而逆天改命。美貌不断带来特权、偏爱和阶级跃升的可能性。
但美貌的权力,从不是女性自己的权力,也从未赋予女性真正的自由和解放。
女生们争相模仿的女明星,都有着一张像未曾受过伤害的脸
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
曾几何时,“荐枕娇夕月,卷衣恋春风”的赵飞燕是美的,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”的杨玉环是美的。而最终,不过是“君不见,玉环飞燕皆尘土”。
上层阶级轻而易举地定义了谁是美的,什么样的形态是美的,美的如众星捧月,而不美的则归为尘土。美又如何?青春娇媚时君子好逑,在朱颜辞镜之后,又会被叹为“美人迟暮”。甚至当定义美的人享用过美色后,还可以说出:“以色事人者,色衰而爱弛,爱弛而恩绝。”
美,从来没有一时一刻属于美人本身。女性之美始终是被凝视的,被欣赏的,被更高权力假装赋予权力的存在。它被禁锢成为一种恭顺和沉默。直到现代社会,媒体和专家们依然指点着美的流行,铺陈着关于美的一切想象,美变得喧嚣,变得人人易得,却依然难以被女性自身掌握。
被曲解的美
在中国的传统认知中,最高级的美是“美而不自知”。庄子说:“美而不自知,吾以美之更甚。”女性的美貌仿佛是一件藏品,与千千万万奇珍异宝并列在这世间,要无知无觉,才方显珍贵。即使女性有了美的自觉,这美也只属于欣赏者——人们传颂着“女为悦己者容”,强调美是向外的。“梳妆打扮”被认为是一种取悦,一种讨好,是一种无人欣赏就不该存在的不洁行为。
左:庄子
右:画家徐操笔下对于旧时女子梳妆情形的描绘
时至今日,依然有人会问那些穿着大胆漂亮的女性:“今晚要和男人约会吗?”如果答案是否,他们会吃惊于她花费这么大力气竟不是为了另一位男性——这不合理,无(男)人欣赏的只能是孤芳。
一句“女为悦己者容”,让“妆容”始终不能是女性自觉。它必须是一种目标,一种使命,即使在今天,也依然被曲解,被赋予太多价值观。
电视剧中女性化妆就被问“是否有约会”的桥段屡见不鲜
(动图出自电视剧《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》)
在当代,我们意识到了妆容与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相关,但却以粗暴的方式将其硬性关联。影视剧总是通过突然红而紫的唇色,凌厉纤长的眼线叠加深色眼影,来凸显一个女性的觉醒——她涂上大红唇,从被人欺凌的弱小女子转身成为大女主了,她不再依附于任何人,她即将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我们看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周芷若,看《甄嬛传》的甄嬛、《芈月传》的芈姝、《楚乔传》中的元淳…当一个女性决定改变,那就先要改变妆容。可这就是妆容对女性的意义吗?这和一个懒起画蛾眉,等待郎君来的旧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左:《芈月传》里的芈姝 右:《楚乔传》中的元淳
你很难看到一个生活中的女性,一个用清淡的妆容、日常的风格来完成自我迭代的女性。我们似乎默认当代女性要成长时,她就要红妆浓颜昭告天下。她只能踩上高跟鞋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敲出声响,只能穿上成套的西装,提高嗓门,用合同敲打桌面,套用一切男性世界里成功的模板。
许多年来,女性只能在有限的自由里表达自我,她的权力、她的野心,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欲念,通通都在“女性凝视”里。即使角色丰富如甄嬛,她也先是懵懂清纯的莞贵人,后是凌厉美艳的熹贵妃,她梳起头发,拉长眼线,涂深唇色,就大杀四方,大仇得报。
甄嬛从懵懂清纯的莞贵人,变为凌厉美艳的熹贵妃
总之,在影视剧的视角下,女性化妆不是为了取悦他人,就是为了向世界宣战,成为进化楷模。女人必须充满目的性地去装扮自己。创作者以为在理解女性,在尊重女性,其实只是再一次用权力赋予虚假的权力。
向内而自美
事实上,大部分普通女性的现实是一片逐渐缩小的、微茫的残境,没有宫廷宠爱与争斗,没有商场如战场,没有价值千万的合同,没有手撕上司脚踩竞争对手。有的只是上班快要迟到,奖金被扣掉了,无休无止的甲方修改意见,家里又哭又闹的两个孩子。有的只是忍下这一切,却仍有人不断地问:“如何平衡家庭和生活?”不断地提醒你:“三胎开放了。”
英国女演员凯拉·奈特莉在被记者问道:“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自己的个人生活的?”时,她反问:“今晚你会问所有男演员这个问题吗?”
这样的她们,很难在美人进化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进化意味着女性成长必须被捆绑在一种大开大合的向外叙事中,要强劲、有力,要敢于画起飞扬的眼线和大红唇才能和一切不公与欺凌对抗。不能怕高跟鞋太响,西服套装太假。要拔地而起,要做爽文女主。
可女性在疲惫中,在沉沦中,在挣扎中坐在镜子前时,只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。遮掉斑点,盖掉黑眼圈,淡化法令纹。那一点点只有自己能发现的精神。女性依靠“妆容”所实现的身份转变,是如此的低调,如此的私密,甚至只是女性之间共情的秘密。她们并不想征服谁,也不想向谁开战,只想让自己不至于此——韶华已逝,可容颜里还要有一点光。
“被禁锢在别人的常识里活着太辛苦了。”
日剧《坡道上的家》截图
女性早就不为任何其他人、任何目的而容了。男性分不清口红色号和粉底的深浅。女性和女性之间,也未必看得清楚眼皮上那小小的一块,究竟叠加了多少巧妙的晕染,腮红又是怎么样偷偷打在了鼻尖上让人显得楚楚动人。一切关于极致妆容的研究,浓缩在了一张小小的脸上,提亮、放大、加深、拔高,仅供自己暗生愉悦。她们的妆容不是争霸,只像是填补了生活中不甘的凹陷。
Kendall Jenner和Kylie Jenner
近期为自有品牌新款彩妆产品拍摄的宣传照
一个全职妈妈,可以跟随着教程完成“女高管妆容”,尽管她此生都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女高管了。她不动声色地坐在家里,就已经完成了隐秘的身份转变。一个女大学生,可以拥有职业妆。一个阿姨,也可以拥有元气少女妆。她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身份,但她们自己掌握美的话语权。
美妆达人小猪姐姐为素人改造的公主妆
普通女性,在生活里必须有这样向内的自美。在无数孤独、无人喝彩的时刻,对着镜子,去尝试自己美的可能性,尝试身份的不设限。美而自知,不为任何收藏者、欣赏者而隐起自我救赎的光亮。
正视“消费主义”
如果说,女性怀着对自己隐秘的爱意,不断走向内在、走向悦己,那让女性再次陷入泥潭的似乎是日渐火热的“消费主义”。
最常见到“宠爱自己”“对自己好一点”这类话语的地方,不是女性的创作表达,而是各种商品广告的宣传语。这已经成为某种流量密码,只要强调这是女性爱自己的表现,产品就仿佛是灵丹妙药——那些不被爱的,孤独的、遭遇着不幸的女性,只需要消费就可以获得幸福。拥有某一款包,就会成为众人羡慕的焦点;使用某款护肤品,就会逆转时光,冻龄永驻。
打着“宠爱自己”宣传语的各种商品广告
这是一种再次将女性向外拉的怪力,让女性远离对美的自觉,远离对内心的探寻,再一次把审视的目光放到外界,让女性被标语化,被赋予虚假的权力。
她当然不应该被消费主义裹挟。不购买某个商品,不佩戴某款首饰,甚至不化妆,都不妨碍一位女性拿起镜子,拿起一些想象,拿起一些对自我身份的期许,往里看,往深处看,用她自己的方式装扮自己。
插画 by Penny
宠爱自己,对自己好一点,并不是只能依靠消费实现。甚至脱离了金钱,一切会有更多想象空间——去交朋友,去彼此陪伴,去大自然行走,去体验未知,那种爱更真实,更切肤,也更难以忘怀。在美剧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中,两位女性角色的成长就源自于彼此的友谊,她们在贫穷中依然找到了美和活力。我们可以通过更多元的女性主题作品,找到消费之外的,多元的自我实现方式,去找到那些丰盈自己的生命,向内自美的真正馈赠。
美剧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第一季(左)和第二季(右)海报
展现出两位女性角色的成长
女性要做的,是去识破那些广告里的虚假关怀,爱与被爱的幻象。不要再听口号,不要再相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你自己去爱自己。在甄别中,在不断地选择中,女性会发展出健全的自觉,健全意味着不再隐藏对美的察觉,也不再将美视为一种工具和手段,美会成为美本身。美会出现在你独自坐下,对着镜子想象自己的时候。
美最终源于一种自我内在的探求,美也终将是女性自我的装点。
撰文-洛怀
插画-Penny
编辑-沈轶、李贝妮
微信编辑-李贝妮
图片来自网络